
决定到成都生活之前,我曾很认真地思考过两个问题。
一,该去哪里看电影?
二,关注哪个平台才可以迅速了解这座城市、获知本地艺文类资讯?
不提前解决这两件事,面对这个新的生活地,我会极度没有安全感。
记忆里,我几乎是在同时关注了两个公众号:叢林(以下简称叢林)和YOU成都。
很难不承认这是过分有缘的事情。毕竟兜兜转转近三年后,我在YOU成都做编辑,这一次的采访对象正是叢林。

叢林
一个创建于2011年4月的非盈利独立文化推广组织,由一群爱电影、爱艺术的年轻志愿者协同运作,旨在通过展映、演出、沙龙、出版和销售等多种途径,发现、整合和推广有鲜明个性的独立文化。
01/
写在见面之前
我对叢林的印象超级好。
作为一个非常讨厌电影院里说话、屏摄、吃东西等行为,以及梦想是在电影院里和ta们打一架、必输也无所谓的人,我第一次去叢林看电影,就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气场——来自每场活动放映之前,主理人查查冷漠且严肃的观影提示。
老感觉不“听话”的观众会被她扔出去,很爽。

·左/叢林主理人查查;右/导演牛小雨
当然,这只是很小的因素,对叢林更多的印象还是来源于更切实际的行为:能持续看到新电影,以及片子很多,竟然,还可以选。
于是,一条固定的#百米小街路线就此生成。
从宽窄巷子B口出,沿路口左前方直走,半路在一家小店吃上一碗担担面、钵钵鸡、麻辣兔头,再溜进红旗买瓶水,继续走到放映现场看电影。

·曾参与过的放映活动之一《成都没有新浪潮 No Wave》,是叢林发起的本土影像发现项目。
来回走上几十次后,心烦意乱时我甚至都想坐几站地铁去这里散步,因为熟。
但在决定采访查查之前,我突然有点慌,毕竟是隔一段时间只因为电影匆匆望一面的人,印象里依旧严肃。没想到,微信刚一加上,她发来的话是:“我认识你的头像,资深观众啊。”
有点诧异的同时,心情有点愉快的轻。
02/
电影,
目光即目的
和查查见面那天,她刚组织放映完年前的最后一次观影:《对望——纪录片女性力量的生根发芽》。
一个名字看起来小众的放映现场,来了126个人。算多吗,算。

“昨天活动非常好,挺有意思。”查查的语调很轻松。因为放映的四部影片之一:顾雪的《家庭会议》,是她一直想放但始终没找到合适契机放的。在女性对望的主题下,有讲亲密关系、家庭关系的相关影片,这才刚好能把这片子放了。
作为观众,我本以为单独放映一部影片是很平常、随机的事,难度远不及系统性/主题性的集合放映,但查查的回答,将之调换了顺序。
为什么要单放某一部片子?契机是什么?观众会因为一个几乎没有知名度的66分钟时长电影单独来一趟吗?这对观众友好吗?……这是作为策划的她要考虑的问题。

·《诗人之血——古涛纪录作品放映+交流》现场,用一个下午,一个晚上的时间放映三部作品。“你可以了解作为一个创作者,古涛在电影制作的不同岗位上如何打磨、塑造、建构一部电影作品,也可以深入体会古涛与众不同的影像风格、电影构成形式以及他对电影艺术性的个人追求。”
以没有什么知名度的独立电影/艺术类电影为工作对象的叢林,不是为了放映而放映,不是为了做活动而做活动。身处这个环境十余年,查查清楚这些没有知名度的电影单放于观众而言是无效的,很难让人产生兴趣。但如果放在某个标签、定位下,一次性从多个维度打开,这样的搭配无疑是更容易被观众接受的方式。

“观众是基础,观众体验不好活动就没法持续做下去。”基于此,12年来,叢林的420+场次放映,电影整体数量则可以在场次上乘约3倍。不同主题下的长片、短片等相关类型的搭配,在足以可见的专业性下,更显温度。
有人根据IMDB估算过世界上的电影数量,这个数字大概是300万部+。首先设置一个议题,再去电影汪洋里翻片子填补内容无疑是一件痛苦的事,往往这样的结果也是影片质量参差不齐。
叢林的放映策划截然相反,是一种很健康的模式。基于大量的阅片量和对各种导演新片的持续关注,查查只需要在日常观影中记录相同的脉络,时机合适,再倒过来直接取一个名字就行。
·叢林和凹凸镜DOC 以“承袭”和“突破”为关键词,梳理近五年涌现的年轻影像创作者,最终选取5部纪录长片,12部纪录短片,推出“赤子之眼——发现纪录片新势力”。
而选片的标准,“新”是查查觉得很重要的一点。可以将之理解为电影语言的新,创作者观看事物角度的新,拍东西的新,表达方式的新。在电影的参考体系里做出新东西,这是放映的标准。

·青年导演牛小雨的首部长片《不要再见啊,鱼花塘》成都放映+导演现场交流。
毕竟要自己看一遍、现场放映给观众看一遍,如果是非常刻板的电影,于她而言首先就会非常煎熬。
03/
放映这件事,
需要做够
更准确而言,叢林的工作服务对象是那些不赚钱、不火、缺乏观众的独立影片。让更多人看到它们存在,一直是叢林的首要目的。
“观众没看到某部片子的时候,讨论都是不存在的。”
在查查看来,对于这种没有大众传播支持、基本上要非常关注电影才有可能知道某部影片、某个导演的情况,首先要有途径去解决可见性问题。同时很有必要的,是把这件事做够。

·在筹划十周年系列活动的纪录片部分时,最初只想将近年没能分享给观众们的影片集中做一次拾遗展播。整理发现,2011 年至今的纪录作品中亦能够识别出一条人生编年的线索。便有了《國人一生——十年紀錄影像回望》。海报设计来自于观众&志愿者。
叢林前二三十期的放映,曾有现场一位观众都没有的情况。查查观察过2015年之前的活动,比如知名度大的万玛才旦三部曲,活动才发完豆瓣就爆了;但只要是不出名的影片或导演,宣传吼得再大声也没用。
转折发生在2015年左右。在持续放映了4年后,首先,在成都,一部分电影院里的艺术电影受众会自然关注到叢林;
其次,那时放映场地换到了明堂创意工作区。这个空间本身就自带流量,喜欢独立音乐的年轻人们常出现于此,他们刚好又是非常理解、支持独立文化的人;
另外,做了几年,查查觉得自己也抓到了一些方法。一场活动的推文要怎么发?发什么?什么顺序结构发?先放影片介绍还是线下观影信息?
虽然没经过验证,不知道这样具体有什么用,但叢林确认了自己的调性。

至此,从宣传到观影体验整个流程的提升,吸引了更多观众。不会再有漏光的酒吧灯光、间歇性响起的咖啡机声,话筒也代替了茶杯,将更大的声音传向了更深远的地方。
而当观众的目光长久地在这些影片中打转,每次观影后,微博上实时搜索到一段带电影名字的观后感,豆瓣看到一条新鲜的评价条目……都是被看见的表现,也潜藏着被更多人看到的可能。
04/
虚头巴脑没用,
那就谈钱
刚刚过去的「2022成都美学大赏」,叢林获得了年度十大人物。
“11年以来,这群年轻人沉默而有耐性地做着非盈利电影文化推广,从小众电影放映、到影像发现计划、纪录片新势力,感谢叢林,每一步都走得具体而坚实。有他们,‘电影不会玩完’。”

正如颁奖词所言,他们的沉默与耐性、对独立文化的长久关注,令所有人有信心。
不止是观众能看到新电影、能有机会和导演现场交流。对于导演而言,在成都,在叢林,放映不缺观众这件事的吸引力同样巨大。
经常看到某影片拿了大奖,但只挣名、不挣钱这件事,确实算不上良好的生态。对于叢林这个非盈利组织而言,收益不那么重要,但变现,对于电影创作者、甚至支持放映的场地方而言,非常重要。

·2019年《二毛》在IDFA第32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成功世界首映。2021年7月,贾玉川纪录作品《二毛》在成都放映+加场展映。
支付导演的版权费、导演来成都参与映后交流的车马费、提供放映的场地方费用、志愿者的费用,以及运营这个组织的费用,怎么都要谈钱。
还好,叢林不缺钱。
十余年如一日的放映电影短片如何挣钱,它的标准、气质准确被越来越多人识别到,有着稳中带新的观众群体,每场活动的放映收入,几乎都会有剩余,在叢林基金里积少成多。
不同于其他民间放映组织的难,这也是查查自己觉得很自豪一点。“做十几年,我没有掏过一分钱,包括志愿者全部都是有收益的,这是我们可以持续做下去的点。”
由此,在想要放映更多影片、邀请导演到场时也变得更容易。更多导演还会主动过来联系,想要在叢林放映影片。

·2022年8月,叢林邀请了《漫长的告白》导演张律,来到成都放映+交流。
查查不会和导演聊情怀,“虚头巴脑的没啥用”,她会很直接地告知会给到一个怎样的费用,往往这个费用对比起来,还很优厚。
并且,如果你有新的表达、新的角度,叢林也愿意用现在有的资源给予创作者支持。
05/
有计划但卡住了,
仍在途中
看起来,一切都是很理想的状态。
但是在聊到观众数量从10到100、场地从小酒吧到大影院的变化时,一些犹疑开始展现。
观众数量越多越好是毋庸置疑的,这直接体现在收益和“让更多人看到”这个目的上。但这种变化会给人抵达某种失衡的临界点之感。
叢林最开始的活动放映场地,在大象酒吧,那时候,现场最多也就来20多个观众。
不赚钱啊,但不赚钱有不赚钱的快乐,它有意思。
讨论的平等建立在人不多的基础上,时常现场的氛围是非常剧烈的,不管有没有导演到场,每个人都可以深度发表自己的见解,同时电影短片如何挣钱,具有社交属性的场子很能交到朋友。

每知晓一个新东西,看到一部新影片,触摸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,那个场景查查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很震撼,“那阵子学都不想上,我每天在想这个事情。”
但百余人的现场映后交流,十几二十个人举手,对于问题的讨论大多就只能浅尝辄止,交流深度不强。并且如果是线上连线交流,在摄像头的另一端,观众在导演的屏幕上只会模糊成一个个小点,很失真。

不能达成有深度的现场交流,翻来覆去地关心表面问题,导演想说的也找不到切口去说,这是查查觉得很痛苦、甚至算得上可悲的点。“但做到这个份上,作为活动方,叢林很难控制说一场能卖130张票的观影活动,你只卖60张。”

一种饱和的、没有挑战性的状态,似乎很难让她再有兴奋、自由之感。
“有计划但卡住了”,很好理解,和我此刻写稿的心情一样。
想要走得更深入、或者关注除电影之外的独立文化也变得非常困难,因为帮更多艺术电影找观众——解决这份可见性就已经是很巨大的工作量了。
在这样的状态下,叢林也在不断尝试,就影片本身、或者说回到成立的动机。
比如平时是更多邀请国内不知名导演,但2019年,叢林邀请了在国际上有同样路径、从独立导演出身的滨口龙介,放映分享了他创作至今的6部短片与4部长片作品,其中317分钟的《欢乐时光》成为了成都大银幕放映史上的最长影片。


·活动的现场图片还被刊印在日本最有历史的电影杂志《电影旬报》2020年3月上旬刊当中。
向观众展示有人也可以做这么好的作品,登上国际大舞台。“我觉得这种激励也不一样。”
并且,叢林还参与出版了1册中国独立漫画选集、做着更多关于独立文化的推广。

·叢林参与刊物《裸体Naked Body: of 》的独立出版事务。这是一本有着超过一百页的趣味十足、充满亲密感、怪异漫画的选集。目前全部售罄。
因此,就算是觉得饱和,但量的累积、和持续的微小变化所给到的奇妙感受,也很动人。
查查还分享了一个AI不能理解的故事:
“每场活动照片我都会传到百度云,有一天,百度云突然就给我弹消息,显示云盘里有500张长得一样的照片,要不要删掉?点进去一看,全部都是从同一个视角拍的照片,我一下就觉得很感慨。
可能对于AI、对没有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人来讲,会觉得好无聊,每次看的场景都一样,放片子+交流,动作很重复。
表面看长得一样,就应该只保留一个吗?这种直接和不理解,对于线下的相聚而言很诡异。
每一场都有新的观众,不同的题材或片子,这些体验都是有价值的,人工智能无法体验的乐趣,是我们做坚持做12年的原因。”
这也和我整理这篇稿件录音的状况类似。一部电影时长的对话,四万多字的录音,文档显示它只有77kb。
@不睡觉 看了都直说“文字太微小”。但文字要继续。
所以,现在的状态也因此不能称之为“困境”,更多是不可避免的,需要去调整、去寻找的东西。
带着存在之必要,叢林继续走在寻找一个路径的途中。
采访当天的天气雾蒙蒙的,能见度不高。盯着车窗外看时,我想起叢林的LOGO也很模糊,这就是他们要的状态,即不提供一个直观的结果、独立思考、自由表达。
采访当天的茶馆环境太吵,临时换到隔壁咖啡店的温室,巧到离谱的,那里刚好是一片丛林。

在丛林采访叢林,字形的复杂似乎在这个空间里铺展开来,它温暖、可见、正是城市生活里的不可替代的自然生态。
电影延长三倍生命,我们在磅礴与浩瀚中见新意、见天地、见人生,再带着本不属于我们的记忆继续前行。
这很珍贵。所以,有人把它从想象里带出来了,我们要享受,也要珍惜。
新年快乐,感谢十二岁的叢林。
●● ●
编辑丨李可以
图源丨小都、受访者提供
找到小都
微信公众号丨YOU成都视频号丨新浪微博丨APP
YOU成都小程序丨YOU在场小程序丨YOU成都抖音
今日头条丨一直播
合作添加微信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END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16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402999666
1、本站资源针对会员完全免费,站点中所有资源大部分为投稿作者付费教程,切勿轻易添加教程上除本站信息外的任何联系方式,谨防被割,如有疑问请随时联系客服。
2、本站所有文章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本站原创发布。任何个人或组织,在未征得本站同意时,禁止复制、盗用、采集、发布本站内容到任何网站、书籍等各类媒体平台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我们进行处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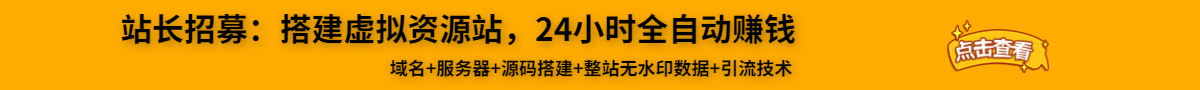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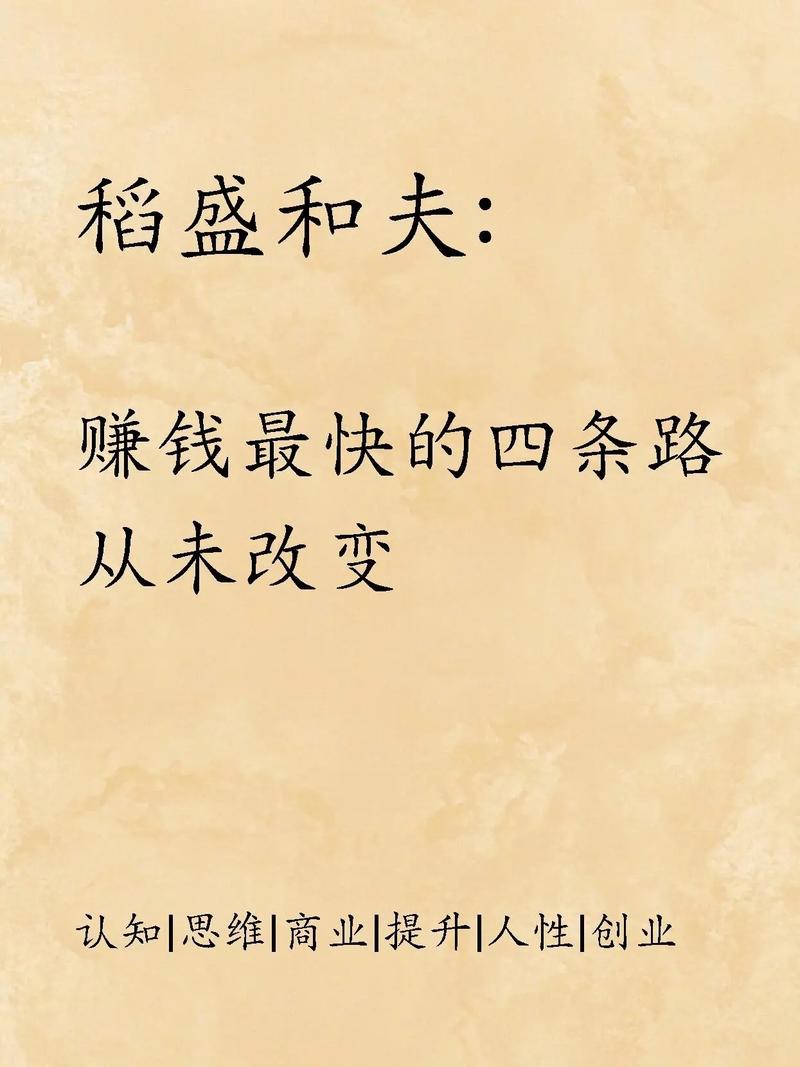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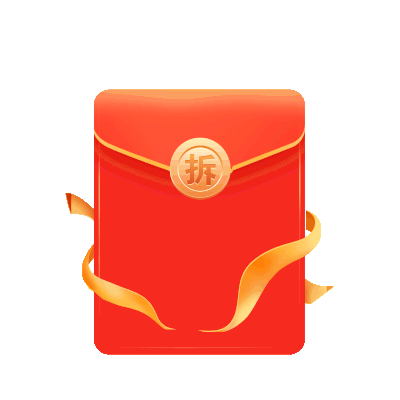 ×
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