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京饭店
文|郝瀚
五
北京时间二十二点四十分,抵达烽火街。路面宽阔平坦,两旁的居民楼低矮而空洞。路灯间距越拉越远,只能依靠相机闪光灯照明。街上空荡,偶然碰到一个女孩正借着路灯的微光看书,翻页的沙沙声真切,女孩都没有注意我们的存在。我拍下她的背影,说,他们可真爱学习。李叔说,当工人的时候,我也爱钻研个东西。电焊、瓦工、木匠活儿都能拿得出手。我爸62年进厂的,一直干到死。李叔伸出手,扶着空气,似乎能触碰到那座建筑,聚集的雾气扭曲了它的轮廓,仿佛随时消散。
李叔说,97年冬天,走之前,我跟东子在道南“老三样”喝了最后一顿酒,每人四两老白干。我到没咋地,这小子喝多了,他喝不了白的,就是陪我。喝完非说去海边。那年冬天贼冷,海面都结冰了。东子比我更想出去,可他挂念你们娘儿俩。最后让我给驮回家,吐了我一后背。晚上我偷偷去对象家,往门缝塞了点钱,不多,是我买断的钱。我心里明白,这一走,就与这一切人一切事都没有关系了。
数次再就业失败后,马慕东开始尝试信仰各种新生活方式。也正在那几年间,马慕东肉眼可见的苍老,视觉年龄起码比我妈大十多岁,或许更多。有时候我妈有事,他就会蹬车前往学校给我开家长会。那时候我已快上高中,萌发出青春期独有的自我意识。虽然我成绩向来不错,但他总能把场面弄得尴尬。每次来家长会,我总觉得背后有人挤眉弄眼,嘀嘀咕咕,暗示我爷挺年轻,一度给我造成极大的心理困扰。我常想以一场斗殴解决,但终究幻化在脑海中。
李叔说,我有技术,用不上,只能卖力气。北京到处在盖楼、拆迁,缺人手。当时比较乱,经常拆了一半,过了半年,一分钱拿不到。当时流行一句话,东西南北中,发财到广东。我就想去深圳,坐了30多小时站票,一开始在罗芳村住,那边好多东北过来的。我认识了一个大哥,姓赵,黑龙江的,之前是看粮库的,闲差,下岗之后来深圳跑黑车。我俩比较投缘,就搭伙开车。他跑白班,我跑夜班。我也没驾驶本,开几天就熟了。那时候关外车少,有时候也到关内。专门拉夜总会喝醉的老板、香港人多,还有刚下钟的小姐。香港人比较大方,还给小费,唔使找啦(不用找了)!有天晚上,拉了三个男的,从福田拉到宝安,他们一直在吵,像广东话,又不像,可能是潮汕话。当时关外还是农村,经过一片果园,没灯,有人说要停车撒尿。我刚停下车,腰上顶了一把54式,就要了点钱。后来我跟赵哥商量,老老实实考了驾照,自己买了辆车。那时候钱还好挣,要不是跑出租,我也不能认识我老婆。她是湖南人,父母都没了,跟他姑妈开湘菜馆,其实就是打工。我总去她那吃盖浇饭,便宜实惠,一来二去认识了。她挺有心眼,但不坏。自己偷着存了一点钱。过了两年孩子出生了,男孩。我俩领了证,凑了些钱,在福田盖了栋自建房,打算自己住。可谁能想到,后来打工的人越来越多,房子疯了似的涨。
“二进宫”后,马慕东开始有组织、无目的地酗酒。其酒友是一瘸子,寡言,因为吊车钢丝出槽,被钢板砸折了腿,早他几年办了工伤内退。此人常年盘踞在小卖部门口的破沙发里,喝本地的秦雪4度,一块五一瓶。大多白嘴儿喝,偶尔在兜里揣几颗花生。那时我上寄宿高中,半个月放半天,几乎都每次都能看到我舅与瘸子在门口把酒言欢,指点江山,缅怀往昔。我低头躲我舅,但他眼神不错,总能招呼到我,说,马奇,陪你老舅喝一个,再跟瘸大爷喝一个。我恨不得当场与之断绝关系,当我跟我妈表示不满时,我妈说,他心里装着事儿呢,让他喝吧。这点我不信服,要说心里的事儿,我跟我妈都比他多。为了供我上学,我妈几乎从事了力所能及的所有行业,在人民广场边上卖炸串;给汽水厂折纸箱子,在商场卫生间做保洁。
后来秦雪黄了,同年瘸子因为脑溢血去世,痛失酒友的马慕东落魄一阵,又迅速振作。每天一早骑凤凰二八车,准时赶往道南那片待拆迁的危房。那边一度集合整座岛城的盲流闲散,大多从事棋牌益智类活动,比如下象棋、斗地主、打麻将。多少带点竞技性质,小赌几瓶啤酒钱。但我舅手臭得像发毛的大酱,三毛一圈的麻将,一下午能输几十,迅速将我妈赞助他的生活费回馈社会。一次大败后,我舅当场急眼,掀了牌桌,质疑他人串牌出千。我舅种种行为,实属赌场大忌,牌友们不惯着,连骂带比划,我舅见势,抄起椅子开抡,不料踩到麻将上大学生能做什么副业转点钱,脚底一滑,当场摔晕。牌友们将他抬进医院,挂了急诊。此前我舅无论怎么作践自己,都没有进过医院,可仅此一次,就顺带查出了癌症,不知是悲是喜。牌友们过意不去,纷纷奉还赌资,毕竟大家有一丁点出路,也不会相聚在这里。我舅态度强硬,愿赌服输,但我妈还是偷偷接了。
我说,我在新闻里看过,传说中的广东包租公,脚踩人字拖,腰里别一串钥匙,开玛莎拉蒂收租。李叔说,没那么夸张,反正够吃够喝,还能把儿子送到香港念大学,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前年查出病之后,嗜睡,老做梦,不吃药又睡不着,头疼。偷偷回了趟老家,自己,谁也没告诉。我先坐飞机到北京,再转车。下了火车我就迷糊了,转盘呢?车站门口的大转盘没了。打车去钢厂家属院,司机外地口音,根本不知道在哪儿。我说,家属院早就拆了,成回迁房了,叫和谐家园,我家就在那。你要是早一年来,厂子还没扒。李叔说,要不我后悔呢,应该早点的。我跟那个司机比划半天,才把我带到铁道根儿那,就是家属院后边,记得吧?
我说,现在那边叫东环路了,水沟也填上了,铁路废了,不过火车了。铁道根儿十几年前且是铁路沿线的荒地,杂草间只有几处拾荒者的窝棚以及成群的野狗。彼时一车车煤炭自山西大同出发,一半留下炼钢,一半从岛城港口出海,散布于南方的发电厂,尽情燃烧,释放能量,点亮东方明珠跟小蛮腰。那片空气中流淌着乌黑的煤尘,荒地间有条臭水沟,不知深浅,冬天会结冰,小时候我舅会带我去捞鱼,放在罐头瓶子养着,活不过一周。再大一点,我就跟院里的野孩子到附近抓蚂蚱、逮蜻蜓,弄得灰头土脸。后来被政府填平,修成环城路一部分,工程历时十年,期间走马三任市长,直到我离开岛城上大学才竣工。
又走了一刻钟,除手机外,其他设备的电量尽数耗完,好在眼睛已适应夜行。柳京饭店显露出完整的身形,李叔解开衬衫,单穿那件印着“建厂廿五周年纪念”的背心。李叔说,铁道都拿铁丝网封住了,但我还是找着了。一下子都回来了。他的声音跟脚步一样没有生机。我说,什么?李叔说,厂长。我立在原地,李叔慢慢走向镜头深处,试图傍住道边的一棵树,像瘫子爬向轮椅。李叔说,如果他没死,我们现在会不会都能过得更好?

六
很想抽烟,手头没有火机。酒保英语很差,我冲他比了一个的手势。李叔说,你想听过去的事。我说,之前听我妈讲,听我舅讲,已经够多了,我想听你的。我心里想的是,这个视频有点像悬疑电影、犯罪片那种,边走边聊,不必刻意,符合我的风格。李叔说,让我想想。三瓶烧酒之后,我搀扶李叔回房间,将他塞进被子。整理了下手机跟相机,纵有20多G素材,却挑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。
第二天清晨六点半,我自然醒来,头脑清晰。李叔正在卫生间洗漱,刮了胡子,穿戴齐整,捯饬挺利索,跟我第一次见他一样。按照日程,我们要花半天时间乘大巴前往南部重镇开城,高丽王朝昔日旧都“开京”,如今的“经济特级市”。作为边境城市,开城毗邻“三八线”,最大看点是板门店,运气好时,能近距离观看南北大兵贴脸对立。
平壤到开城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路,约200公里路途,行车四小时左右,传说中的低速公路。路况不太理想,时而土路,时而是柏油路与水泥路的拼接,把三魂六魄颠出人体。或许因为工作即将结束,小金心情不错,盘起的头发披散下来。全团的大爷大妈在呕吐中丧失活力,小金试图调动大家情绪,说,小金教给叔叔阿姨们两句朝鲜语好不好呀。没人搭腔。小金说,好,第一句,你好,安宁哈西蜜瓜,跟我念。安宁哈西蜜瓜。几人稀稀拉拉的响应。我说,叔,你听吧,一会儿她指定说,哈密瓜加上西瓜。小金说,教给叔叔阿姨一个窍门,哈密瓜加上西瓜。
批判完美帝造成的半岛民族分裂与历史创伤之后,小金也不再解说。沿路设了不少检查站,岗亭里有背着冲锋枪的人民军,约靠近边境越密,车只好走走停停。窗外风景相当原生态,苍山翠树,几无人迹。大约一个半小时后,大巴经停一处类似高速服务区的地方,路牌用中文标着“沙里院”。路边泊着一溜旅游大巴,几张蓝色防水布撑起的雨棚下,身着统一制服的售货员正叫卖水果饮料面包以及各种纪念品,无数中老年同胞挤在摊位前,像国内农村大集。因为晕车,我下来透气。朴恩淑跟小金正一起转悠,看来全西山饭店的旅行团日程都差不多。小金从钱包里掏出一张美元买了瓶可口可乐,她看到我试图拍下这一幕,便躲闪了一下,有些害羞。卫生间边上,罗马尼亚兄弟正对着抽烟,我又套到一些实用信息,一是要等所有旅游团回到酒店再行动,不然很容易被刚回来的导游撞到;二是要天黑行动,从酒店花园里的小路走,隔离带有一道豁口可以出去。我再次诚挚地邀请他们加入,两兄弟瞥了一眼朴恩淑,说,祝你好运。
越过“三八线”后,满目刚抽穗的稻田随风摇曳。板门店停车场比打仗时还热闹,小金说,情况特殊,到这里小金就不带大家了,接下来请听从指挥。取代小金的是两个军人,一个负责讲朝战历史,另一个同声传译,一唱一和,声调激越。由于此地较为敏感,全程禁止录像拍照,索性我也懒得深入,蹲在树下抽烟,研究地图,规划路线。小金看着地图,说,想象比现实会更好吗?我说,有时候是这样。小金说,可现在你已经到了。我说,我看过一部电影,叫《共同警备区》,里边有板门阁、蓝房子,特别感人,虽然我知道那都是假的。小金说,中国电影吗?我一时语塞。小金笑了笑,说,你去看看李叔叔吧,他一个人在车上,你们可是9号家庭呐。
回到车上,李叔看着我手中的地图,说,我想好了,你带我走,按你的来。我说,我会把过程拍下来。李叔说,这是你的命。我说,什么。李叔摇摇头,说,脑子不管用了,有些事要慢慢来。我说,好。李叔说,我还没问你,东子他过得好不好。我想了想,说,那看跟谁比了。李叔沉默。我又想了想,说,谈不上多好,但也没有坏到没法收场。
1998年春天,马慕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主动买断,从大连屯了批日本关西进口麦饭石磁疗床垫,自封总代理,面向退休的中老年客户。又印了几千张花花绿绿的小广告,力争贴上每根电线杆。广告声称床垫可以改善血液循环、调节体内磁场、促进细胞活性。销量看涨后,我舅盘下工人文化宫,挂上横幅拉花,改做会场直销,积极拓展业务范围,广泛征招次级代理,赚取加盟费。广告也开始宣称能有效治疗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甚至癌症。直到工商局突袭会场,当场没收全部床垫。事实上,床垫是旅顺小作坊产的,质监局检测显示,躺上边睡一宿,辐射量约等于一气儿扫3000次CT。念我舅初犯,缴纳罚款又痛快,只拘了七天。出来后,我舅瘫床上半个月,仅靠白酒维持生命体征。虽然我记得他之前只喝啤的。
午饭设在开城市区的一家外宾饭店,说是市区,基本都是黄泥路。饭店照平壤的条件直落几档,所谓顶级在地美食“皇帝铜碗”花花绿绿,其实还是泡菜开会。不光李叔,全团大爷大妈都没胃口。想到晚上不知要走多久,我还是干了两碗米饭。饭后取消休息,直奔高丽博物馆,象征性地参观一圈,然后立即返程。李叔竟一反常态拉我下车,说想去看看。在作出决定之后,他的心态似乎轻松了些。小金代我们领票,在门口略作介绍,放我们自行参观。据说此地有千年历史,前身是高丽王朝最高学府成均馆,地位堪比北京的国子监。内部形制仿照孔庙,单缩水几圈,有几座低矮的朝鲜风格建筑,基本是高丽人参及周边产品售卖中心,人参酒、人参烟、人参糖、人参护肤霜等。团里大爷大妈常年走南闯北,除了围观,没人掏钱。李叔尤其对“高丽皇家安宫牛黄丸”感兴趣,售货员汉语标准,话术硬气,三万一颗一口价,真到生死关头,一丸续命还阳,绝对物超所值。几个北京大爷面色轻浮,表示同仁堂的可比这便宜。我再次想起马慕东,如果这颗价值三万元的牛黄丸漂洋过海,滑入他的胃袋、溶入他的经脉的话,他的肺叶是否会恢复弹性,脸颊是否会富有血色。
回程时,我戴上耳机,逼自己眯一觉,积攒些体力。我劝李叔也休息会儿,李叔表示已经休息够了,让我继续讲马慕东的事,我只好拼命地回忆。“一进宫”后,马慕东买断工龄的钱所剩无几,又管我妈借了点,攒了辆“狗骑兔子”,在火车站附近跑活儿,起步五元,二十封顶。所谓“狗骑兔子”就是农用三轮罩上塑料顶棚,比喻形神兼备。第二次自主创业对我舅来说无疑是下行且残酷的,或许他一直对床垫的事耿耿于怀,脾气越加乖张,常因块八毛钱跟乘客当街对骂。或因为一单小活迁怒于昔日的工友、今日的同行。天长日久,我舅在黑车界人缘耗尽,不是今天气门芯让人捅,就是明天顶棚让人划,但每天生活尚能勉强维持。如此司机生涯持续到北京奥运会前,彼时市精神文明办大力“创城”,街上交警比行人还多,专逮没牌儿黑车。我舅凭借意识跟身手,钻小路、走地道,照常出车。他是在我中学附近十字路口落马的,据我妈说,那天面对警用摩托追捕,我舅火力全开,如舒马赫附身,为避闪刚放学的孩子,一个急转扎进路边的书报亭。
李叔没有对我舅的生活做出任何评价,但他不知从哪摸出一小瓶人参酒,酒体浑黄,浮着一株参。我说,叔,这几天看你就没断过。李叔说,在家喝得更多。说着,李叔就着一片药一饮而尽。我说,这药吃多了上瘾。李叔说,还剩最后一片了。直到马慕东病逝前,他一直采取保守疗法,不化疗不开胸,靠吃李叔同款的止疼药过活。马慕东查出病的时间,大抵是我刚上大学那阵,与此同时,我们家的生活有所转机。鉴于我妈长久以来的英明教导,我高考比较理想。出分后,她豪掷巨款咨询一位初中肄业的“报志愿专家”,并开出几个硬指标:一大城市且离家近,意指北京;二重点大学,有面子;三专业要硬,给当官打基础。以妈的想象力,只有清华北大、最多人大才能算是大学,所以一开始她很难认可民族大学,让她自洽的是法律系。很长一段时间,她沉溺在百度搜索中,逐渐疯魔,神秘兮兮的告诉我她的最新研究成果,百分之三十五点七的大领导都是学法律的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有零有整的数据是如何推算的,即便如此,比率也不算乐观。另外一件事是我妈的长线投资见效,化纤厂职工宿舍拆迁,到手回迁小两居一套和五万补偿款款,自此不必跟马慕东挤在钢厂家属院住。这一投资可追溯到化纤厂改制之初,她硬挤出八千块钱,从一个工人手中买下自建房的产权。卖家恋旧,连地砖墙皮窗户都抠走了,这么些年我们也没钱住进去,被左邻右里当成笑料。种种表明,我妈所做的一切不但能站住脚,似乎还有些超前。如果按照她写好的剧本,会在我取得户口,工作稳定后卖掉房子,再添上全部积蓄,供我在北京交首付,然后门当户对的相亲,优生优育一个宝宝。但某种本不该存在的某种力牵引着我,纵然我拼尽前半生去远离这一切。
李叔安然睡去,泛红的薄暮中,将迎来我们在半岛最后的夜。大巴车沿着青春街驶入西山饭店,此时是北京时间晚十八点十五分整。我要将所有设备充满电,放下一切不必要的东西,因为这条路不知要走多久。随之而来的是超越身体的厌倦,那是精神的耗散,意志的虚无。我叫醒李叔,说,叔,成与不成,就看今晚了,等时机一到,我们马上出发。

七
四周只有李叔的背摩擦树皮的声音,镜头跟随他,直到他缓缓滑落。画面上是李叔面部的特写,借着月色,李叔眼底血丝虬结、渗出殷红的斑,像酒精中毒,亦或颅压飙升。哪怕架在稳定器上,画面还是在抖,我有点举不动了。我说,叔,干这个真他妈累,回北京我就不干了。李叔说,好,回家好啊。李叔闭上眼睛,说,厂长人不错。上班都从家里带饭,就那么几样,吃的也不多,难怪他那么挫。现在叫啥,代购?碳钢鱼竿,托人在港口俱乐部,跟一个日本跑船的水手那买的,钓黄花鱼,百试百灵。后来办完事,觉得晦气,想扔了,一想小半年工资,我就送给你舅了。
钓鱼确实成为马慕东最后几年中的重要构成。一是海边空气更好,能稍微缓解咳嗽;二是他已无法从事任何体力劳动。与其说他钓鱼,不如说鱼钓他,每每枯坐一天后空手而归。有时碰到熟人,会送他两只螃蟹。在岛城,螃蟹就两种,圆壳长斑叫花盖儿,两边尖的叫梭子。我舅没生病时爱吃花盖儿,母的多,蟹黄也多,一只起码能下半箱啤的。我对他的钓竿没有印象,但此物尚存的可能性不大,要么被我妈收起烧掉,要么拆迁深埋地底。
李叔说,后来我就不吃鱼了,煎炸炖烤,老闻见一股人血味。那时候我刚搞上对象,打算倒插门,女的家里条件不错,在港务局当会计,人胖了点,有福相。反正我叨咕半天,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进去。那天我喝了挺多,风一冒,脑子清醒,身上打摆子。无冬历夏,他吃完饭就在家门口后边的铁道根儿遛弯。那年雪特别大特别白,连铁轨都没了。他就在铁道根儿那转悠呢,嘴里念念叨叨。李叔捶打着头颅,仿佛与某种寄生其中的怪物搏击。他从兜里摸出最后一片药,就着最后一口酒吞下。李叔说,我跟他说,不能买断,我该结婚了。我能有个家不容易。厂长说,名单还没出来,兴许没你呢。就算有你,买断也没什么不好,你还这么年轻,也没有牵挂,条条大路通罗马。当时他还说什么来着,效率优先、兼顾公平,韬光养晦,有所作为。说他老家有个亲戚在深圳跑出租车,一个月挣两千块钱。我当时想了半天,深圳不挨着香港吗?那旮说鸟语,听不明白。我就想干炉工。当时我有点急,拿鱼竿照他后脑戳了一下,寸劲儿,一下子就他妈躺地上了。没见血,但是人搁地上抽抽,嘴里吐白沫,红虫儿似的,鱼食儿,你知道吧?我探了探,感觉他没气儿了,也可能是我手冻僵了?
血无声息从李叔的鼻孔涌出,顺着脖颈,地下暗河般蜿蜒,侵染了背心上“廿五”两个字。我指了指鼻子。李叔低头看了看,眼神涣散,戳着太阳穴,说,长了个瘤,橘子那么大。压着中枢神经了,得开颅。我有钱,也有医保。我把水递给他,说,冲冲。李叔似乎很热,拧开瓶盖,当头浇了下去,蒸汽盘旋在他头顶。李叔说,想想还是算了。这两年我老瞅见他,有时候自己喝酒,刚闷了,杯就满了。一转头,他就坐我旁边,带个破逼头盔、穿身埋了吧汰的劳保服,举着酒瓶子,搁那叨叨,说贼鸡巴热,感觉要化了。一开始我有点害怕,后来习惯了。再喝的时候,大不了也给他摆一副碗筷呗。他不喝酒,直勾勾盯着我。说自己冤枉,时间一到,所有人都得买断,他自己也买断,但总得给愿意干的人留点念想不是?他早就知道,但市里领导的决定,又能如何?他说他原谅我了,让我逢年过年,给他烧点纸钱。再有条件,就去看看他。其实我挺后悔,觉得他死了一了百了。可厂长死了,还有部长,部长死了还有主任。
副厂长失踪后,生死簿随他而去,或许这玩意压根没存在过。工人们松下口气,现实是自打年后就没再开支。积蓄耗光后,有人另辟副业,钓鱼、种菜甚至去北山上打兔子卖,无力开源的人只好去市场捡烂菜叶、火车洒落的煤渣,每天因为势力范围干的头破血流。一时盗窃猖獗,保卫科作为主力,默许这一切。先从值钱的下手,钢材、铸件、焦炭。下半年厂子彻底停产,仓库里吃灰的劳保服、大头鞋、防爆头盔,甚至手套、目镜一箱箱往家搬。当时全市的半大孩子不论男女,脚上人均一双不合脚的翻毛钢头鞋,包括我在内。打架神器,踢人巨疼。1998年夏天,钢厂正式宣布破产,从上到下集体买断,随即是我妈的化纤厂漫长的改制。
我说,尸体呢。李叔说,开始想扔海里,那年大寒潮,海面都封上了。又想扔火车上,但当时过的车越来越少,又是年关。转炉一年356天连轴转,死了人都不带停。那天正好东子值班,我找他商量。我其实也没说啥,就说,东子,回家过年吧,我顶你这班岗。我俩啥关系,不用说了吧?厂长贼瘦,跟袋料差不多,轻飘儿。当时咋形容呢,像热油锅里炸茄子,上边水没擦干净,刺啦一声,钢水崩在我脖子上,我隐约觉得他挣扎了一下,还喊了一声。我老梦见这一幕,嗷一嗓子把我吵醒了。
1996年的除夕夜确实给我留下几处记忆点。一是赵本山的小品《三鞭子》大学生能做什么副业转点钱,讲修路的事,台词经典:老少爷们儿搭把手,抬起头,往前走!二是那年我第一次喝白酒。起因是我妈把鸡冠子摘给我,但我从小就讨厌吃任何与鸡有关的东西。她说,小孩吃鸡冠,长大当大官。当时我确实想当官,起码校长级别,这样上体育课绝对没人敢扒我裤子,便强忍恶心吞下去。我妈心情愉悦,独酌一盅老白干,用筷子头沾了给我咂摸。许是酒精作用,没撑到难忘今宵,我就昏倒了。三是我妈、我、马慕东头回一起过年,这个习俗从那年起,一直维持到他去世,毕竟此前他都在值班。大约零点,孩子们冲到院里放炮,朦胧中马慕东的身影在门口徘徊,但我无法确定他刚进门还是准备走,我挣扎着爬起来,想去摸他的兜儿,把一切掏出来。可眼皮一坠,竟有千斤重。
李叔皮肤通红,濒临燃点,脸上又湿又黏,分不清眼泪还是汗水。李叔说,后来我开始找那炉钢,托了好多人。一直在厂里耗着,被偷走了不少。没多久厂里停产,凑了5000吨。因为杂质不过关,跟一批铝材、钢化玻璃贱卖到这,最后盖了这柳京饭店,还他妈烂尾了。想想挺鸡巴有意思,他也算变相支援世界社会主义建设了吧?
我说,还能行吗。李叔扶着树干,像刚睡醒的考拉。身后两道短促的喇叭声划破夜空,一辆出租车缓缓停下,国产比亚迪。小金拉开车门,说,9号家庭,跟我回去吧。我本以为她会发脾气,可她只是面露疲态,说,柳京饭店就这么吸引人吗?我说,抱歉,实在不好意思。小金说,没有关系。不过,你们是我见过走出去最远的,也是最奇怪的。
小金拉开车门,我只好上车。但李叔仍望着那幢建筑。隔着窗子,听不清李叔跟小金的谈话。司机轻点喇叭,伸出头与小金交涉,语气所有争执。但我不确定,毕竟韩国电影里男女谈恋爱说情话都跟干仗似的。李叔也上了车,我闻到一股腐烂橘子的味道。司机没有调头,直勾勾蹿出去。我说,回去吗?小金叹了口气。
柳京饭店地基打得很高,两条车道盘桓延伸,直通往正门的台阶,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抽烟。小金说,抓紧时间吧。仰视大楼,光色变幻,直插天宇,令夜空更低沉。小金想去搀扶李叔。我拦住她,说,让他自己去吧。眼看李叔几次摔倒在台阶上,又颤巍着支起来,喊,来了!来了!此时是北京时间凌晨,景观灯一齐关闭,刹那间通体黯淡。我打开手机,用仅存的电,拍下《半岛之夜》摇摇欲坠的结局。
色彩消退,万籁寂灭,一切褪色为黑白默片。玻璃幕墙海浪般翻滚,层层叠加,像人体衰老松弛的皮肤,汇聚出泄露脆弱的纹饰。冰河解冻,骤然爆裂,亿万点渣滓折射出无数点月光,飞逝为蜿蜒飘忽的烟尘。结构是巨人的骨架,看似强硬却被大卫一击而溃散。骨片在千万温度炙烤下,迸发钢的魂灵,铁的意识,水般流淌,汹涌的热量转瞬吞噬一切。被掏空脏器的胸腹中,只余存空洞的夜矗立着。李叔从画面中缓缓滑出,我一遍又一遍搜寻,直到他完全消失镜头里。那是所有影像的终点,或与这夜永为一体。
The End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END 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限 时 特 惠: 本站每日更新海量各大内部创业教程,一年会员只需168元,全站资源免费下载 点击查看详情
站 长 微 信: 402999666
1、本站资源针对会员完全免费,站点中所有资源大部分为投稿作者付费教程,切勿轻易添加教程上除本站信息外的任何联系方式,谨防被割,如有疑问请随时联系客服。
2、本站所有文章,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,均为本站原创发布。任何个人或组织,在未征得本站同意时,禁止复制、盗用、采集、发布本站内容到任何网站、书籍等各类媒体平台。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,可联系我们进行处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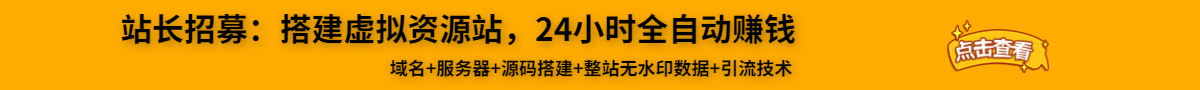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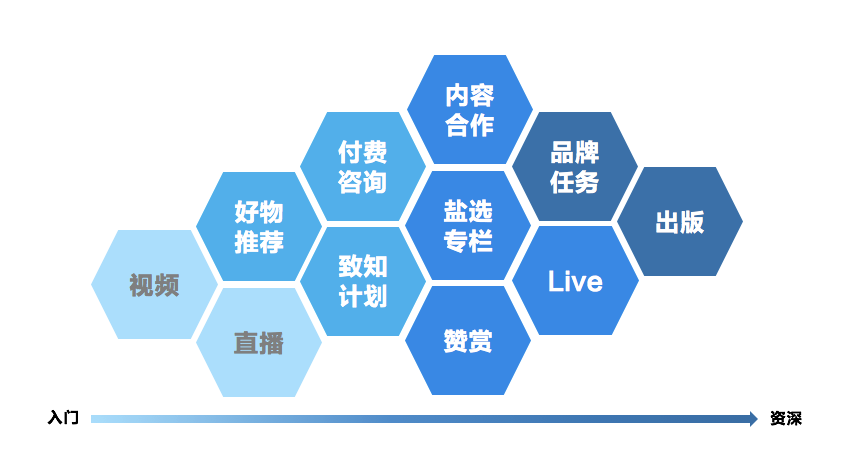
 ×
×